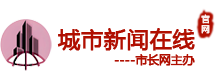又见老张,是一个下着雨的周日。偌大的校园里走进去两个人连一丁点声响都没有,雨水浸泡着的肃穆在这个季节带着一点凉意。老张的步子很大,在铺了草质的地毯上溅起许多水滴。
上了楼,摸出钥匙,打开房门,柜子里是满满当当已经烧制过的泥塑,工作台上散放着好几个正在修正的瓷枕娃娃泥胚。
我叫住正要去张罗着烧水的老张,我抽烟,不喝水。我找个凳子坐下,老张在几个柜子里翻找他在艺术节上参展的龙凤瓦当。三彩的瓦当确实漂亮,烧制技术也达到了很高水平,观感似瓷,触摸如玉。
我对艺术品的喜爱远胜于物质和名利。但对老张的艺术品,我更多地希望它的物质价值大于它的艺术价值,这或许源自内心深处对一个身处困境却依然不改对艺术痴迷的老人的偏袒吧。我知道老张家里的情况,大儿子多年患病生活不能自理,去年没了。已经在轮椅上坐了好几年的老伴儿也总会在每天上午的11点钟给他打电话,该回家了,老伴儿饿了,一个人在家里也着急了。说到老伴儿的电话,老张还是蛮理解的,至少可以提醒他该吃饭了,忙起来的时候,他会忘了喝水,忘了时间。
泥塑是和泥巴打交道,比不得玉石金银那些金贵的东西。但泥塑不靠模具,全凭一双手和深藏在头脑中的记忆,它不全是一种技术,更多地是一种智慧,是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再造。老张痴迷泥塑的原因也大抵如此吧。
同老张相识源自泥塑艺术,却高于泥塑艺术。平凡人身上那种为梦想而奋斗的坚韧像一道奇异的光,深深吸引着我。
记得德伟在新闻上推出老张在实验小学给孩子们上课的图文的应该是在2019年,随后在会涛、向前这些比较玩得来的朋友们的引荐下,更多的媒体朋友都深度加入进来。我算是相对核心的几个,但也是贡献最小的一个。我的自媒体平台本就是纯文学性质的,社会关注度不高,影响力也不大。尽管也是尽了力的,心中还是有诸多的过意不去,总觉得有愧于老张在夜里送我的那匹陶马。他的不易总令我心生怜悯,他的诚意又令我不忍拒绝。
他们那代人,尤其是搞艺术的,把人情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今天的谈话,我与老张坐的很近。也许是这个原因,谈话的内容也很私密。谈到了他严厉又敬佩的父亲,谈到了他睿智又能干的母亲,谈到他十二三岁还在上学的时候拉脚的往事,谈到过往错过的机遇和诸多失败的遭遇。在谈话中老张几度落泪,我却没有去中断或者安慰。我太了解他此刻的感受了,他需要倾诉。这么多年来憋在心中的委屈,终于找到一个突破口可以宣泄。
这是一种历经千辛万苦终于看到曙光时的悲喜交加。张开双臂,哪怕是凛冽的寒风都可以紧拥入怀。
我关注的是他的生活,他关注的是泥塑非遗的传承。谁邀请都去,免费去。谁来都教,免费教。
我很郑重跟他说,“法不贱卖,道不轻传。”至少,象征性地收取一些劳务费,不过分的。他答应我时眼睛下垂,声音很小。我知道,他并没有听进去。他已经彻底被艺术给收买了。
天空依然下着雨。老张大步走在前面,右手微微抬起,像是提着一盏老旧的马灯,整个校园一下子温暖起来,同样温暖起来的还有这位老艺人业已布满皱纹的脸。
谁又能给他的马灯里添些油,让他的艺术之路更亮堂一些,让他的非遗传承更久远更宽广一些呢?
相对于泥塑技艺传承,我更关注他的生活。
(文/卧龙)